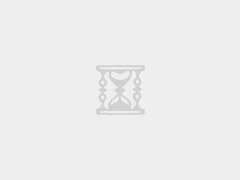中国古代社会给人的印象,往往是秩序井然的、是礼教森严的,乃至使人们认为,缺乏自由,似乎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,但这不免是一种偏见。我们今天当然在呼吁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,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够尽情释放。但这并不等于说,自由在传统文化里就是缺失的。恰恰相反,自由,在国学里也随处可见。
一
心灵自由
道家的生命理想最接近自由的状态,老子的一个重要观点,就是要“道法自然”,意思是说:大道之行,既要仿照大自然的规律法则,又要效法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状态,顺其自然,这就是道之所在。
老子鼓励人们找回自然原始的本心、顺应心灵的自然感召——这不正是最大的自由吗?自由,就是一种随性而为、不受拘束的状态,而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,让自由贯彻得如此彻底!还有什么准则,能比认可每个人自身自然而然的发展状态,更自由更舒适的呢?
而把道家思想与个人生命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、更为艺术的庄子,对自由的感受也更为强烈。一篇著名的《逍遥游》,其实描写的正是庄子心灵的驰骋、是庄子思想的放飞。《逍遥游》中描述的那个叫做“鹏”的大鸟,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,能够背负青天激越云间,上可飞天下可入水,自由往来于天地间。其实,庄子哪里是以如此瑰丽的笔墨来仅仅描写一只鸟的行为呢?文中的“鹏”,正是庄子自己的心,那是一颗开阔六合、涵纳古今、超越世俗、纵横时空的心。
心的自由,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。人力所能永远是有遗憾的、人生环境永远是被设限的,然而,心的开阔可以超越现实局限,自由翱翔在无边无际的精神世界。
心之大,才是人之大;
心之自由,才是生命之大自由。
所以,虽然庄子把他的生活状况自比为在泥里曳尾涂中的龟,却把他的内心状态自命为鹓鶵之凤,高飞于空、不染纤尘;虽然庄子度日时的家境贫困要不得已去借粮,但他在酣睡中却能潇洒做一个名垂千古的美丽一梦,梦到自己变为蝴蝶翩翩而飞。甚至,“庄周梦蝶”的自由洒脱,使他在醒来后不知梦里梦外、孰真孰假,不知是庄子变成了蝴蝶、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。这种奇妙的精神体验,正是因为他的心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出神入化之境。
庄子能以一具受现实艰难拘束的身躯,放飞起一颗自由快乐洒脱的智慧心。他这种身心状况的反差,也很像是儒家学派里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的行为,孔子曾称赞颜回说: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,人人都不堪忧苦,只有颜回不改其乐——他不改其乐的,也许是身在陋巷、心在书香的精神享受,也许是身在平凡、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,也许是身虽未动、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。
可见,在中国文化里,无论是入世有为的儒家,还是出世无为的道家,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有何不同,但是在内心和精神层面,他们都同样拥有着自由的灵魂、都同样构建着独立的人格,都可以因为心的独立自由而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。不管成功还是失意、不管腾达还是穷困,他们能够不以客观好坏为枷锁,靠自我主观撑起蔚蓝的天。
不自由的心,在鸟语花香中也能画地为牢;而人生任何形式的牢笼,都锁不住一颗真正自由强大的心。
二
生命自由
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影响极大的两大学术流派,他们的观点和表现看起来往往是对立的,比如:
儒家主张入世,道家注重出世;
儒家呼吁积极有为,道家喜好清静无为;
儒家重视集体利益,道家推崇个体精神;
儒家从家庭走向社会,道家从社会回归自然;
儒家努力兼济天下,道家追求独善其身。
可以说,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,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;儒家担负着家国天下的责任耕耘人间,道家遵循着生命本源的朴素超脱世外。
看起来,儒家比较沉重受缚,而道家比较轻灵自在。但其实,作为各自成熟的学问体系,儒家和道家的圣贤,尽管外表形式有别,内心却是一样的自由无拘束。
比如孔子形容自己,是“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,到七十岁的时候,他已经修炼到了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人做事,然而再怎样任性而为也都在合理规矩之内,不会逾越禁区去触犯规则、冒犯他人。这难道不是人生最理想的自由状态么?他已经完全超越了社会的一切限定、束缚、刻板、教条,那些禁忌都不会让他感到受限、为难,相反,他可以自由地驰骋于人生,却于规矩礼教秋毫无犯、于人际往来言行适度,他能成为一个最快活舒服、也最令他人感觉舒服的人。
所以,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,还是仰望天空的道家,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。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,他们都毫无异议地认为,不管在朝堂、在闹市还是在山林、在陋巷,都可以、也都应该,自由而活。
甚至,提倡法制、法度严明的法家,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。自由突显出秩序,在有形的层面,所有的自由必然都有其边界,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,那么相对应的,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。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,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。所以法家的“明法度”,其实是更好地规范了“享自由”。
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,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够充分体会到自由,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,甚至是具有艺术性的。中国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。
所谓“大隐隐于朝,中隐隐于市,小隐隐于林”,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、受朝堂之艰险、受宦海之沉浮、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、受到制度禁锢、受到官场奴役、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,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,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、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——他们总认为,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,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,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逸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。所以,他们选择在任何困境里都去努力自我调节,他们写诗、作画、弹琴、读书、品茶、赏花、雅聚、清谈……这些内容都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。
他们有一片美好的隐士山林,就在自身的书房里;
他们有一片理想的世外桃源,就在自家的花园里;
他们有一片放松自我的精神沃土,就在自己笔下的诗文里,尤其那些田园诗、山水诗、风景诗,都带领这些文人寸步不离闹市而尽享山野田园之乐。
对外,他们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;对内,他们书诗文之美而养其心。种种陶冶心灵的行为,就是他们官场的后花园,就是他们生命的自由国。
对于懂得自由的人生来讲,不能解甲归田,那就耕耘心田、培育精神家园的心花怒放;不能吟游四方,那就心怀天下、培养人生大观的游目骋怀。
在他们可能四处碰壁的生活中,自由却可以无所不在。
国学中的自由,是儒家责任里的闲情,是道家朴素中的安然,是法家理性下的游弋,是士人重压时的释放。自由,从来不在远方的乌托邦,而就在当下的轻安自在;自由,从来不依靠他人给予,而全在于自我获得。因为,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,抵得上心灵自由的强大有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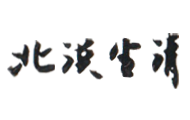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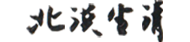 北漠塵清
北漠塵清 微信关注,获取更多
微信关注,获取更多